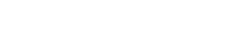“石碏谏宠州吁”----春秋乱弹之四
发布时间:Jan 14, 2021 | 作者:淇县文化馆 阅读次数:8次
《春秋》也好,《春秋左传》也好,都试图占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居高临下地把道理说给千秋万载的人们。因此它们的许多文章都要在叙述的基础上融合说教的说辞,以把儒家的思想与实践得以结合验证。但是实际上它们的很多文章往往在喋喋不休地说完大道理以后,忘记了与实践相印证的初衷。
象本文中的石碏,他在劝谏的时候其实犯的就是这样一个错误,光有理论,没有事实论据,如何能让庄公认识到溺爱呢?巨大危害呢?而“石碏谏宠州吁”这篇文章本身也在犯同一个错误,交代了事件的起因,然后大篇幅整理了石碏的说教,之后就草草了事,匆匆结尾了。而最能验证石碏理论的正确性的后面的远远强于雄辩的事实部分却被忽视了。
其实后面的故事远比前面精彩。
即位卫桓公似乎是个很平庸的人,但是即使是这样平庸的人也明显地感觉到了他的弟弟州吁给他的皇位造成的威胁了。在桓公即位之前,庄公因为州吁喜欢军事,已经把州吁封为大将,给了他一部分兵权。那个时候的大多数国君为了保住自家的江山,一般都是把自己的后代封为朝中的大臣,来协助自己的大儿子巩固地位。但是那种情况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孩子们必须是团结的,否则就是自作主张地替下一代分配权力的蛋糕,分散了后任国君的权力,一个不好,就会弄巧成拙,导致兄弟之间为争夺皇位而相互残杀的流血局面。
以州吁的专横跋扈,自是不会把桓公放在眼里,那么他们兄弟君臣相处的状态就可想而知了。桓公即位的第二年,就罢免了州吁的大将职务,收回了兵权。州吁和石厚等一干死党逃往国外,四处流浪。流亡期间还因为同病相连而与郑国的流亡王叔段和公孙滑等人结交为朋友。
前文中说过州吁从小就是就喜欢舞枪弄棒,与其一同逃亡的也都是些好勇斗狠、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州吁在外逃亡的十几年间,又结识了不少臭味相投的狐朋狗友。十四年后,州吁、石厚等人纠集了一帮杀手偷偷潜回卫国,伺机刺杀桓公。适逢周平王去世,州吁打听到桓公即将赴周奔丧,于是设下埋伏,终于将他的哥哥桓公刺杀。之后谎称桓公因病去世,临终将王位传给州吁。事发突然,卫国的臣民还没有反过味来呢,州吁已经迅速办完手续,登上了王位。桓公的儿子公子晋逃亡到邢国避难。
这一年,就是周郑交质那一年,郑国刚刚抢了中央政府的粮草,郑庄公正与大臣商议去洛阳朝周之事呢,有卫桓公讣音传来,得知是公子州吁弑君篡位。要说这郑庄公也真是个人物,立刻说: “吾国行且被兵矣!”群臣问郑庄公:“主公何以料之?”庄公说:“州吁素好弄兵,今既行篡逆,必以兵威逞志。郑卫素有嫌隙,其试兵必先及郑,宜预备之。”
和郑庄公所料完全一致,州吁即位后,朝野都不服气,沸沸扬扬的都是些戳州吁脊梁骨的言论。州吁很郁闷,此时已经官至卫国上大夫的石厚给州吁出主意说,国内的情况现在已经这样了,要想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咱们就要出兵找个诸侯国打上一架,这样在转移国内注意力的同时,也能威慑那些乱说话的人。州吁说,你说的容易,周围的诸侯没有惹咱们的,这仗哪能说打就打的起来啊?那石厚微微一笑道,您才做了几天国君,当然没有人惹咱们了。可是我记得咱们当年在外逃亡的时候,咱们卫国为了咱哥们郑国的公孙滑和他老爹段的事情,跟郑国打过一架来着。现在咱们得势了,不如就拿郑国开刀好了,正好也替老滑出一口气啊。
要说这个石厚也算是个人才了,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转嫁国内矛盾、凝聚国内民心的办法也旧似乎近代和现代才被统治阶级熟练运用的。而石厚提出的向郑国开战的建议在一举两得的同时,也充满了冒险精神。因为郑国无疑是当时最强盛的诸侯国之一,老虎的屁股可不似乎人人都可以摸的。我因此推断州吁的刺杀行动恐怕也是石厚全力策划和参与的。
石厚当然不会傻的以卫国这点兵力去征伐强大的郑国。石厚有石厚的办法,他打正了替段讨还公道的旗号,亲自去说服宋、鲁两国。对宋殇公时利用了宋殇公的那块心病---寄居郑国的子冯;对鲁国的时候,则贿赂了掌握兵权的大将公子翠;对陈、蔡两个小国则直接告知要讨伐不仁义的郑国。由此组成了五国联军开始了讨伐之战。
郑庄公可不是吃素的,那是老政治家了,说到打架,他可是行家里手,说到权谋,那也是玲珑心肝啊。对面五路诸侯的肚子里面各自怀着什么样的鬼胎,庄公心里面那是溜清,他早看出州吁约来的那四个诸侯国里面,也只有宋国似乎因为顾忌公子冯,是真心想打这场仗。州吁不过是为了立威才来讨伐郑国的,而且州吁刚刚上台,立足未稳,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打下去啊?这仗还有什么不好打的?
郑庄公派大夫暇叔盈带一支军队,把宋国在郑国政治避难的公子冯护送去了长葛,然后派使者告诉宋殇公:“公于冯逃亡到我国,我国不忍杀他。令他前往长葛待罪,您自己去处理吧。”宋殇公果然移兵去围长葛。蔡、陈、鲁三国之兵,见宋兵走了,都有了撤退的想法了。没等走呢就听说郑国公子吕出来迎战,三国都袖手观之。
石厚引兵与公子吕交锋,还没怎么打呢,公子吕倒拖着画戟跑了。石厚缴获了些郑军的粮草,并不追击,而是传令班师回国。州吁没搞明白石厚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石厚说,你没见宋国已经跑了吗?剩下这几位也就是些敲敲边鼓的水平,郑国这么强大,我们自己哪是人家的对手啊?现在我们有了打败郑国的威名了,这趟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还是赶紧回国处理过内的事情吧,时间长了不回去,我怕家里出事啊!
州吁打了个激灵,忙不跌地撤军回国。一看正主走了,陈、鲁、蔡三国乐的不用动手,自然也是高高兴兴把家还了。这厢里联军一撤,郑军没有了后顾之忧,那边围攻长葛的宋军可倒了霉了,两国鏖战自不在话下,后来郑庄公去洛阳朝见周王,采纳祭仲的计策,假借周王号令纠集联军,一口气把宋国打的大败,孔父嘉死,宋殇公亡,最后公子冯回国即位,郑、宋两国遂成同盟。这里就不一一细表了。
得胜归来的州吁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地位得到了多少的巩固和拥护,和石厚两个人一嘀咕,想起了已经告老还乡多年的石厚的老爹石碏,有这位前朝的德高望重的老臣支持的话,还有谁敢说三道四呢!于是准备了礼物派石厚回家请老爷子出山主持大局。那石碏听说儿子石厚竟然协助州吁把桓公都杀了,正在家里的堂屋里来回踱步呢,听说儿子今趟回家是想请他出山,心里冷笑着,脸上却不动声色,告诉石厚说,我这把年纪了,还想多活几年,你回去告诉州吁,就说我得了慢性病,让他另请高明吧。
州吁没有办法,对石厚说,你爹不来就算了,那你倒是问问他老人家我们目前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啊?好歹让他老人家给指条路啊!石厚无奈,不得不再次回家问石碏。此时的石碏心中早已经有了计较,对儿子说,你们去朝见周王就是,如果他接见你们君臣了,那自然是承认你们的地位了。不过这办法也有坏处,万一周王不接见你们,就弄巧成拙了。石厚一听老爹似乎还有下文啊,接着问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让周王接见他们。石碏微微笑着说,我的老朋友陈国君桓公一向得周王偏爱,你和州吁先去趟陈国,央求桓公为你们出面游说周王,大事可成!
石厚大喜,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亲爹会处心积虑地算计自己,还以为得了什么金玉良言,遂与州吁去了陈国。那厢里石碏早派人给陈桓公送去密信一封:“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实弑寡君,敢即图之。”要知道陈国是州吁谋杀的哥哥卫桓公的母国啊!陈桓公对州吁和石厚两个人早就欲杀之而后快了。这下两个人居然自投罗网,而且还有石厚的老爹照应,断了二人的后路,这样的爽事要不做是要后悔一辈子的。待得州吁和石厚一行来到陈国后,陈桓公立刻设计将二人擒下并分押两地。
消息传回卫国,石碏立刻入朝与文武百官商议,后派卫国大夫右宰丑和石碏家臣獳羊肩前往陈国。右宰丑杀州吁于濮,獳羊肩杀石厚于陈。左丘明修传至此,称石碏:“为大义而灭亲、真纯臣也!”这就是成语“大义灭亲”的来历。州吁死后,卫国上下从邢国迎立流亡的公子晋为国君,就是卫宣公。
读完州吁的故事,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郑庄公。
历史总是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话真的不错。看过“郑伯克段于鄢”的朋友一定会发现州吁的故事和郑庄公的故事也是这样。郑国的段和州吁一样都不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但是都一样从小受就受到父母的无比宠爱;在自己的哥哥登基后,一样产生了篡位的念头并都有了实际行动;都曾经流亡过外,在国外的时候也都没有过放弃;在他们流亡的时候,都没有得到哥哥锄恶务尽式的追杀。
不一样的是结果,段篡位行动失败逃往国外,在国外仍然贼心不死,曾经纠集外国军队讨伐母国,但是他在利用别人的同时也是别人利用的对象,没有得逞;州吁逃亡14年也一样没有忘记篡位,幸运地刺杀成功,成功谋取皇位。当然在这些不一样的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不一样就是,州吁并非段那样的庸才,而且身边有一帮有本事的哥们儿,相反地,段的哥哥庄公并非象州吁的咯咯那样脓包,这才是段最终没有成功,而州吁可以有一举得手的重要原因。
现在我们推敲的是导致这两个篡位事件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前面说的做国君的哥哥没有对逃亡的弟弟斩草除根。
庄公没有下手杀弟弟,但是在历史上还是落了个处心积虑、姑息养*的罪名。我们一定记得左丘明煞有其事地指点庄公的建议: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我们以前批评过这种所谓的“亲亲之道”,但是还没有实际的论据,现在有论据了,就是州吁。再想想《春秋左传》里面只记录了石碏进谏的那段话,而不以事实验证其正确性,难道真的是一个小小的低级失误吗?
郑庄公不追杀弟弟,任由段在国外不断做着颠覆国家的串联,不过是为了一个名声。卫桓公不杀弟弟,想必也是一样的原因,但是他太脓包,所以被人家反噬一口,连命都丢了。以“亲亲之道”来规范和评判政治斗争,本质上是混淆了政治手段和道德行为的界限,没有看清楚封建社会家族统治的实质。而在儒家的道德观体系里面,君臣关系分明又排在父子关系的前面。这就充分体现了儒家道德观的虚伪性,同时这种虚伪性又是导致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却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看见儒家学者通常只能就事论事,一事一理,常有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就是这个原因。那么联想一下现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种种不可理喻的现象,思考一下儒家文化对过去和现在的深远影响,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所感悟呢?
第二个问题,说说教育孩子的问题吧。
我们发现段也好后于也好,都上一被父母宠爱,最后走上不归之路的。这即使对于我们现在的做父母的人,也不能不说是一个警示。在这个故事里面,卫庄公宠爱州吁本来是人之常情,自己的孩子嘛,哪有不宠爱的,孩子多了的时候,总有对撇子的,难免会厚此薄彼,这是人之常情。但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明白规则更要让孩子明白规则,宠爱不是无限的,是有一定范围的,超出了感情的范畴,影响到他人的生存甚至社会国家的政治生活了,就突破了道德的藩篱了,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家族统治的社会或者说集权社会的统治者最容易犯类似的错误,把感情和个人好恶与权力分配联系起来。因此,所有的封建社会和集权社会的正常运转都需要托福于最高统治者的智慧和开明。推而论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无论是在封建还是在集权社会,都要把儒家那套“礼”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至少名义上是这样),在法制不完善或者存在先天的不可克服的情况下,儒家的“礼”自然而然地成了香饽饽。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以德治国吧。
卫庄公对州吁的宠爱,在一些事情的处理上是缺乏全盘考虑而只顾及了个人的感情。州吁的成长是一个大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庄公的宠爱。父亲的宠爱小儿子,本是人之常情。我们且把宠爱放到一边,庄公在教育的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宠他你干脆就立他为太子好了,这样至少还可以保护一下恒公这个同样教育失败的儿子。桓公是子,是贵,是长,是亲,是旧,是大,是义,教育的失败之处在于没有把他教育成一个强势的人。州吁“名”又没有,因为做不了太子,“实”又强势得很,名实不符,不出问题才怪。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里面所反映的教育后代方面的问题,最应该思考或者谴责的恰恰不是庄公的溺爱州吁,而是石碏对儿子石厚的教育,那才是最失败的教育。卫庄公溺爱州吁,州吁之不肖,是可以想象和理解的。但是石碏是知道应该怎么教育孩子的,其子石厚却助纣为虐,与州吁同流。
你看看石碏在劝导庄公的时候一套一套的,把人家说的一个楞一个楞的,人家不听,他还不愿意。我因此相信庄公并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而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所以说石碏进谏的言辞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用这样的言辞显然无法打动庄公听从他的劝导,也就是说,他的话并没有切准问题的要害,没有挠着庄公的痒处。也可以这样理解,石碏自己并不是很明白教育孩子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他真的明白其实的关窍,他自己的儿子石厚就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因此他不知道怎样劝导庄公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这就是教育孩子的最根本的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不是教育方法的问题,那些东西谁都知道,不见得都能教育好孩子,是什么问题?是怎样处理教育者的感情和理智的问题!打着感情的旗号,很容易使教育者自己对孩子的感情在方式上形成一种习惯,而习惯本身就是一种放纵。放纵感情是一种仅仅顾及了教育者自身的自私的不负责任的短视行为,尽管双方都可能得到暂时的愉悦,但是在这种愉悦的麻醉下,双方总有一天都需要为这种放纵埋单,而且是双份的。
在这个故事里面,卫庄公支付的帐单是两个儿子的生命,石碏支付的帐单是亲手杀死儿子的生命。只不过,以石碏的老谋深算(你说他老*巨滑也不冤枉他,最贴切的应该说是生姜老的辣)和霹雳手段,多少捞了点本回来而已,杀了亲生儿子,赢得了个千古流芳的美名。可是从教育孩子的角度来看,从“亲亲之道”来看,石碏所谓的“大义灭亲”实在是不值一晒。